
中国古代文人画是推崇的是“无我”“忘我”的境界,是“拟物移情”的美学观。到了黄宾虹这里,他大胆突破所谓“物象”的束缚,也摒弃了他自己前半生所致力山水写生、敬习古人的努力,开始追求内心的造化以及强烈的情绪表达,也即从“物象”转移至“心象”;气象万千,皆源于用心。傅雷曾说他“似近似于西欧立体、野兽二派”——当时在留法的傅雷可能过于自信想展示他的西方艺术史学养,故提及了彼时在欧洲盛行的立体派、野兽派,但从今天的视野来看,他的知识面显然还是有局限的,也即以法国20世纪初的流行风格来比照黄宾虹的艺术,当年信息流通也极为有限。笔者倒是认为,若一定要有一个同时代的比照,黄宾虹的努力更近于表现主义的精神——一种尊崇内心真实情感而在画面表现上又非常简洁有力的视觉语言。
在骨子里,黄宾虹实则将中国绘画大大往前跨了很重要的一步。他接续明代文人画的精神,在“无人之境”上走得更为深远——从古人“拟物移情”的“无我”到黄宾虹的“从心而发”的“无我”——此二者在本质上不同,黄宾虹的“无我”更具有艺术家的主体意识;这种主体意识依托于敢于突破陈规的实验性精神,更是深厚学养和博学视野所催生的自信与智慧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黄宾虹和张大千的故事。同样也在晚年画过黄山汤口的是张大千。那是1963年的秋天,时年已经65岁的张大千正在巴西圣保罗城自建的中式庄园八德园中作画,画了一套《黄山山水册页》,其中包括《汤口》《七里泷》《清凉台》《剪刀峰》《严陵滩》等12幅。 其中,大千在《汤口》一画的题跋中写道:“游黄山有多途,一从钱塘江溯新安自汤口入,一从宣城太平经焦村翠微寺入。二十年前吾曾三游兹山,皆从汤口。”——这是否可视为张大千在以画、以文巧妙地为黄山作广告宣传呢?而早在1930年张大千32岁的时候,他就和张善孖、黄宾虹、郎静山等发起组织了旨在开发建设黄山的“黄社”,号召所有社友皆以绘画、摄影、诗词和文章等为黄山作大规模的宣传。张大千甚至还出过一本《张大千黄山摄影画册》专著。以及,张大千生前最后一幅未完成之作便是黄山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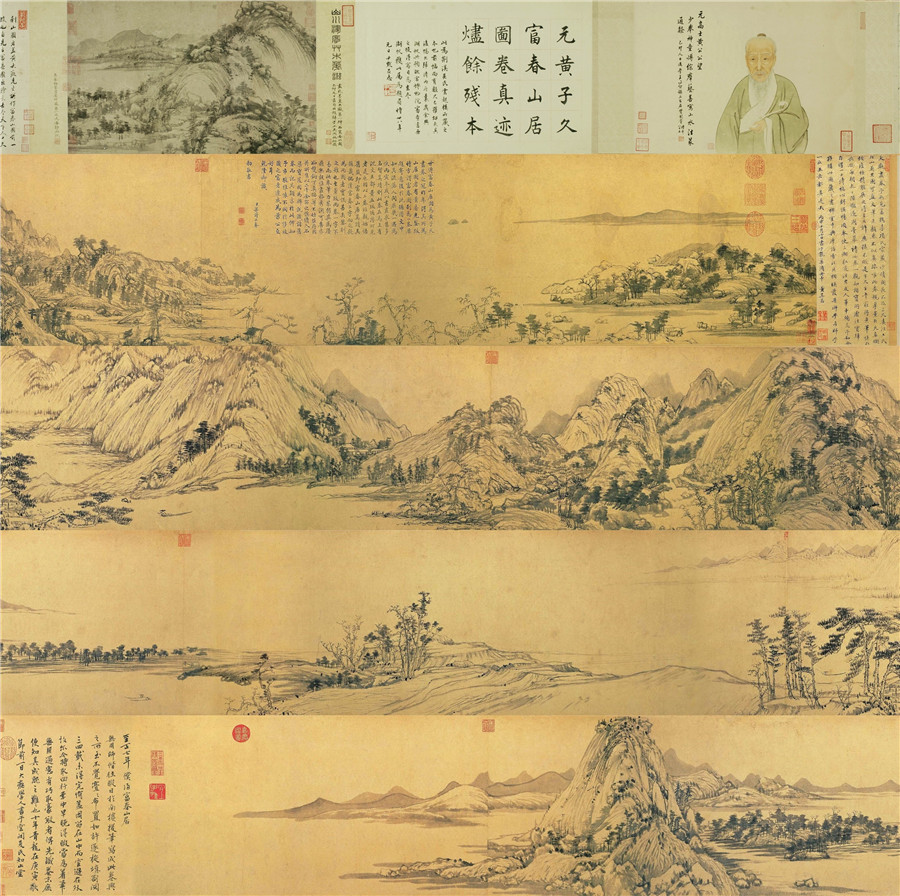
绘画既是一种独立自足的艺术行为,也是一种能够沟通人物、地方、历史乃至天地乾坤的方式;是主体思考的结果,是人文主义的视角,更是学者型文人精神的诠释。这一独立自足的行为也是提倡一种理性的、科学的、敬畏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历史——不管是“我们”的,还是“别人”的,首先应该有一个“大同”的视野。其次,中国文化向来智慧柔韧,有庄子的“道”,有孔子的“知”,是“解衣磅礴”与“知行合一”的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混合。在当代,我们尤其需要唤醒这种骨子里的精神传统,并在当下的时代发扬光大——这不应只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实实在在要去做的事情。
时光的桨声灯影,船过无痕;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在运动中的,我们不是一叶扁舟,我们是头顶星空、脚踏大地的人类,总是希望能留下痕迹,为着我们今天的时代,为着汩汩而流的大国文化。“欲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源泉。”——而艺术,无非是以有涯之生,追求无涯不败的美与力量。

或许,这就是我们今日重走黄公望之路的初心所在——不仅是黄公望,还有那些为艺术的美与力量不懈追求和探索的大师们,他们的精神一直如灯塔般照耀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。
(林霖)
[1]转引自汪世清《<江山雪霁>归尘土,鱼目焉能混夜珠——记中国绘画收藏史上的一大骗局》,原载《新美术》1996年02期,第21页





